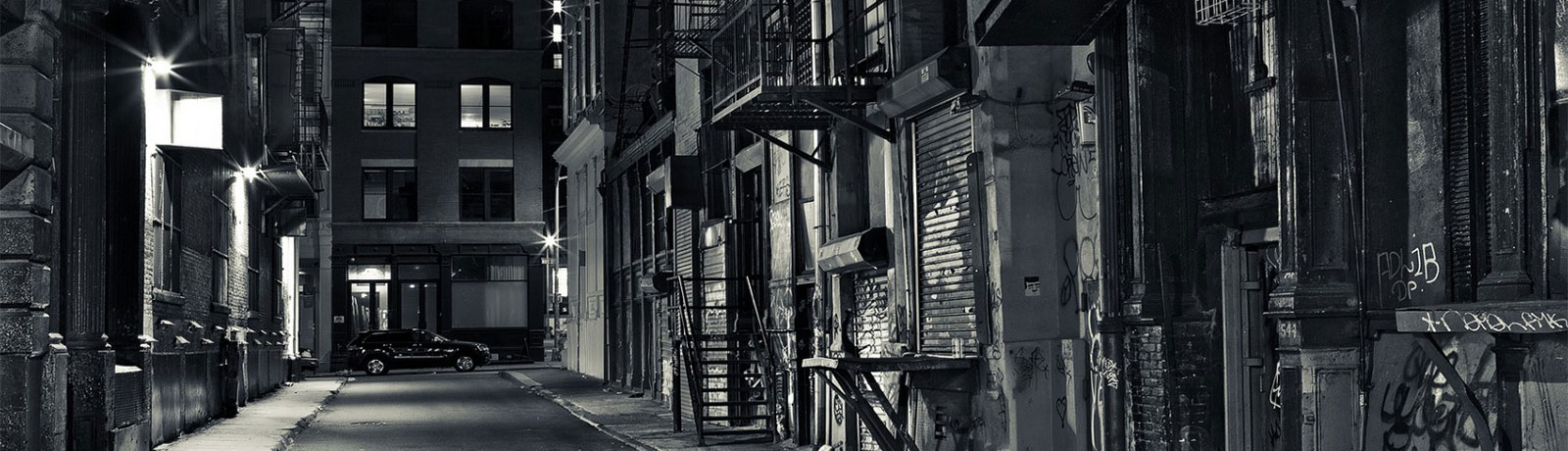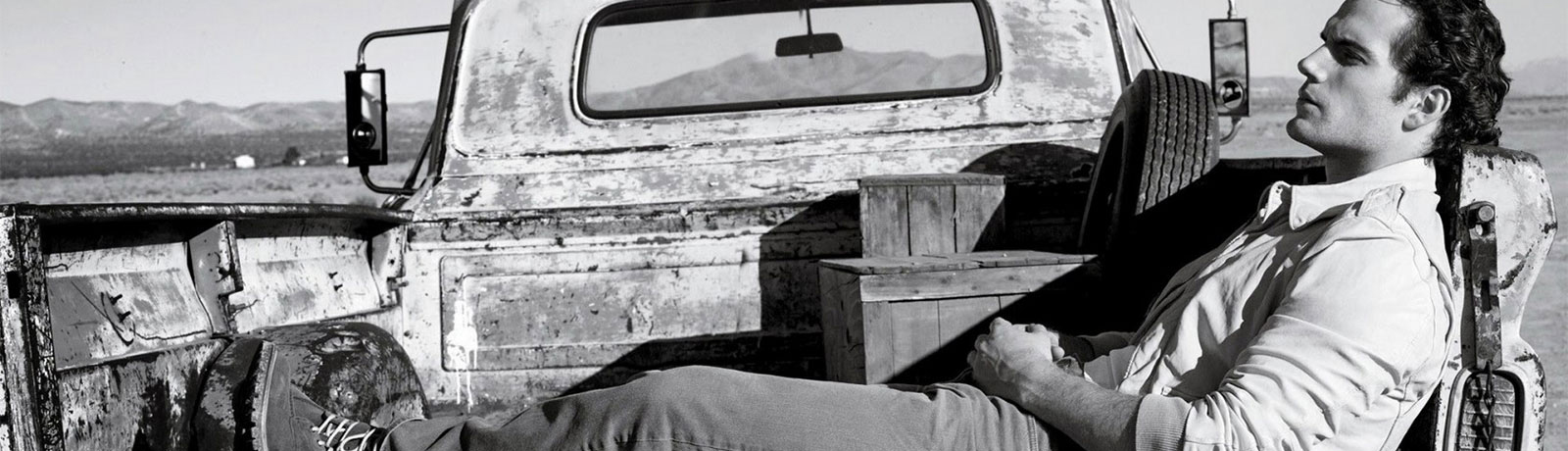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教育补习活动和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大规模发展作为一种教育现象,在我国逐渐受到关注。由于学生在完成学校课程后还要参加培训机构的课程,无疑增加了他们的负担。那么,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是否应该存在?如果应该存在,那应如何净化整顿教育培训市场?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当下我国不少省市已经开始着手治理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国外在这方面的治理经验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国外对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界定
国外一般认为“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主要是指以营利为目的,面向中小学生,以提高学生成绩为目的,对学生进行学校课程补习和升学辅导的机构。究其本质,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属于“补习教育”(Supplementary Education)的一部分,也有学者称其为“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补习教育有两种主要形式,即非正式组织的家教(Private Tutoring)和机构化的校外培训(Cultivate Training),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就属于后一种。
需要声明的是,对于补习教育,各国的习惯用语有所不同。国内习惯称校外培训为“培优”、“辅导”或“代管”之类的动听或不敏感名称;在一些英语国家,人们经常使用“私人教导”(Private Tuition)、“课堂”(Classes)之类称呼,组织补习教育的机构称为“学习中心”(Learning Center)、“专业学校”(Academies)或“学习所”(Institutes);在日本,教育补习机构则被称为“学习塾”(Juku),根据具体功能的不同,“学习塾”可分为3类:以指导学生升学和参加各类考试为目标的“进学塾”,以辅导学生校内课程为内容的“补习塾”,以学校落后生为教学对象的“救济塾”。[1]
二、各国治理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举措
教育补习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特别是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更为普遍。而最近几十年以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此现象都日趋普遍。在法国、埃及、印度、马耳他及罗马尼亚,超过1/3的学生经常接受教育补习。[2]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属于补习教育的一部分,因此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和补习教育政策密切相关,本文以各国政府对补习教育政策的探讨来分析各国治理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举措。
(一)忽略放任型
一类是主动不干预政策,这类国家信奉自由市场经济,并认为自由竞争能调节补习的负面影响,应该把它留给市场去支配,而政府的介入可能会使教育补习市场产生混乱,这方面的代表有加拿大、德国等国家。另一类则是由于国家能力不足的原因,无法实施有力政策和监管补习教育,缺少整体的规划,只能任由补习教育自行发展,如柬埔寨、越南。
在世界范围内,采取忽略放任型的政府可能是最为普遍的,但对主流学校课程难度和进度的影响、家庭教育成本的增加等因教育补习带来的消极影响应引起足够重视。
(二)由禁止转向管理型
该种类型的代表是韩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开始对补习教育进行改革。1980年提出的《7·30教育改革》的目标是要完全控制课外补习,具体措施有:增加大学入学考试次数以减少考试的激烈竞争程度;成立教育管理委员会系统以提供低价的课外补习;所有大学生和学校教师一律禁止提供有偿的私人课外补习;学校禁止开设学术科目方面额外的高中课和课外补习等。[3]但事实上,家长、学生对补习的广泛需求确实存在,禁止政策并未起到实质性作用,补习教育禁而不绝。